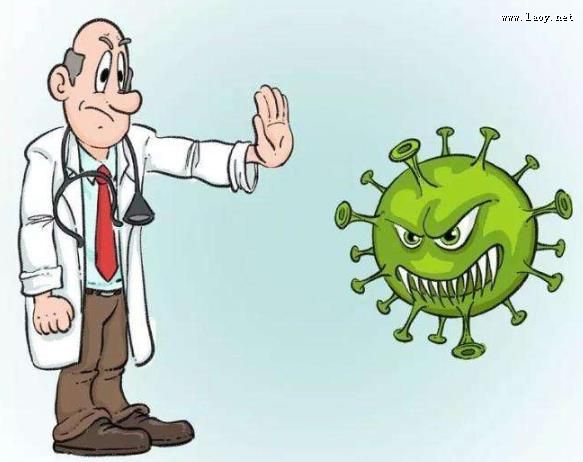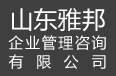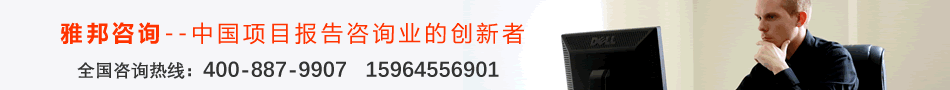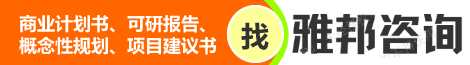“在嚴峻挑戰的國際背景下制定”
王文:中國制定政策時會把加強頂層設計和堅持問計于民統一起來。2019年底,中央就已召開研究部署“十四五”規劃編制專題會議。近一年來,我也有幸受聘成為兩個部委與一個西部省份的“十四五”規劃咨詢專家,切身體會到中國這樣的大國制定“五年規劃”的復雜性,特別是未來五年規劃中還要有全球視野。
羅思義:要理解這個五年規劃在中國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就必須了解中國所取得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就。1949年,新中國幾乎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從我掌握的數據看,當時只有10個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于中國。毛澤東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說的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不是空談,誰能想到,僅僅70年左右的時間,也就是幾乎一個人一生的時間,中國就將在下一個五年規劃期間躋身世界高收入經濟體之列。此前,中國在改善衛生健康狀況、提高預期壽命、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等眾多領域也都取得了成就。
威廉·瓊斯:中國正在制定的下一個五年規劃將與以往的規劃有很大不同。我認為,受疫情的影響,在全球經濟一段時間內不會出現任何實際增長的時候,中國正在制定一項影響中國和世界未來若干年的計劃。而且,今年的重點將不再是單純的數量指標,而是更多地著眼于在技術和生產力方面創造質的“飛躍”。
羅思義: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的“十四五”規劃不僅對中國發展,而且對全球都具有里程碑意義。當然,中國的短期經濟前景比其他任何一個大國都要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在2020-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將占全球經濟增長的60%,而新的五年規劃也代表著一個根本性的轉變。
按照中國自己的標準,2020年中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同時也實現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但大多數國家在進行國際比較時都采用世界銀行的分類,即將經濟體分為低、中、高收入群體。按照這一標準,在下一個五年規劃的中期(2022-2023年),中國將進入全球“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實現這一發展水平,決定了“十四五”規劃的性質。早前中國的五年規劃是為了“擺脫不發達”,而這次規劃將以建設高收入經濟體的不同任務為中心。
此外,“十四五”規劃是在人類面臨嚴峻挑戰的國際背景下制定的,這其中有美國的因素,有西方國家未能控制住疫情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有氣候變化的威脅等。
王文:除了你們談的特殊意義,我還有一些感受。通過在全球治理領域的研究與國際比較,不難發現“十四五”規劃所體現的鮮明中國特色。
首先要提的就是全面性。“十四五”規劃與中國過去的五年計劃或五年規劃一樣,都是匯集全力,群策群力,前后須花一年左右的時間制定,盡可能地體現全國民眾、各個產業、區域、機構利益與訴求的最大公約數。當下中國,東西部區域發展、城鄉發展、貧富者之間的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仍很突出,要求“十四五”規劃的制定更加精細,盡可能充分考慮與糅合所有民眾的利益交集。在我看來,中國的五年規劃與美國或西方其他國家的“四年戰略計劃”“總統施政綱要”完全不同。歐美選舉政治容易產生愈演愈烈的利益集團的固化與分化,一黨支持的政策往往就是另一黨反對的。
其次是持續性。“十四五”規劃承前啟后,是在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重大設計,延續著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的發展任務,承接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重要使命。在編制中,必須考慮國內發展與全球秩序劇烈調整背景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比如,全球經濟放緩、國際不確定性加劇,“十四五”規劃就必須考慮全球化有可能逆轉、國際分工發生重大調整的邏輯,尋找關鍵產業鏈的區域協同與新的全球布局。再比如,在檢驗“十三五”規劃完成進度時,會發現生態、扶貧、消費結構等領域的明顯改善,但也需要看到如營商環境、科技創新仍有待加速提升的內生壓力。過往檢驗與未來設計,都需要考慮延承度,這與西方國家“一屆政府一組政策”的慣例完全不同。事實也證明,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出現了嚴重“內卷化”狀況,即無休止地循環重復,導致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更高的發展狀態。

“會體現生態文明和科技投入”
王文:剛才我們都提到“十四五”規劃還有前所未有的“全球性”考量。中國要深刻認識到未來五年極有可能是矛盾與風險多發期、共振期,同時也要意識到中國已從過去的“跟跑者”“搭便車者”升級為“領跑者”“被搭車者”的重大轉變。因此,“十四五”規劃還要有著引領經濟全球化的設計考量。因此,中國“十四五”規劃一定會強調實操性。“十四五”規劃編制既要考慮預期完成的可能性,更要顧及“十三五”規劃的完成進度;既要考慮當下面臨的重大戰略機遇,更要防范在復雜國內外環境下的潛藏風險。它不是像西方一些國家那樣“是的,我們能”“讓國家再次偉大”之類的夸夸其談,也不是空有對國民許諾的空頭支票,而是扎扎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前行。
羅思義:有的問題與外部問題重疊,是人類共同的問題,特別是氣候變化。中國此前曾在概念上提出“生態文明”的目標。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期間,中方提出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西方著名的經濟分析人士和歷史學家亞當·圖茲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上撰文說,中國這樣的承諾重新定義了人類的未來前景。如何實現這些目標,一定會體現在新的五年規劃中。
威廉·瓊斯:是的,毫無疑問,“十四五”規劃還將強調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并為實現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鋪平道路。中國在擺脫化石燃料方面比美國走得更遠,中國的做法不是像一些西方環保主義者提出的那樣減少人們的消費,而是朝著新能源邁進,最重要的是發展核能工業。中國在法國的“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計劃”上的重點參與,以及在合肥開發自己的核聚變反應堆,凸顯了中國對推進新能源的決心。
我還想補充的是,中國經濟要保持穩定和提高增長速度,關鍵在于科技投入,這將是“十四五”規劃的重要內容。科技投入會帶來創新,進而影響到整個經濟全局,創造出更高的經濟效益,并普遍降低生產商品的價格。深圳以其快速的增長速度成為這一政策的典范。中國共產黨還承諾創造更多的“深圳”。自從提出“四個現代化”戰略目標以來,科技一直是中國經濟的支柱,但以今天科技的發展,變化的速度幾乎是天文數字。鑒于美國現政府一直試圖將中國高科技阻擋在全球市場之外,這一政策對今天的中國也尤為重要。中國實際上正與美國在科技領域展開競爭,為了保持其發展勢頭,中國必須“挑戰極限”。
“雙循環是條正確的前進道路”
王文:說到“挑戰極限”,有德國媒體近日在報道“十四五”規劃相關話題時說,“熱衷于發動對華新冷戰的美國政府看上去既沒有戰略也沒有戰術,相反,中國有中長期的發展規劃,如目前正在制定‘十四五’規劃,起草該五年規劃是一項漫長而微妙的任務,意味著未來中國要大力振興國內市場,更強調開啟一場全新的‘質量持久戰’”。
羅思義:中國在取得驚人成就的同時也面臨新的挑戰。有些挑戰是內部的,高收入經濟體要比低收入或中等發達經濟體復雜得多。但也有一些是外部的,美國已開始試圖阻止中國發展的路線。正因為如此,被熱議的中國“雙循環”經濟概念在新規劃中才顯得如此重要。許多美國分析人士認為,現政府在攻擊中國時犯了嚴重的戰術錯誤。美國政府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是個錯誤,因為關稅是由美國人民支付的,而且美國攻擊的是中國強大的、美國無法競爭的、優質的中等技術制造業。也有些美國人認為,美國的攻擊應該集中在中國的強項上,即高科技上,應像對待華為和字節跳動那樣,集中力量削弱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因此,特朗普和拜登都被敦促對中國實施“技術封鎖”。
當然,美國能否實現這一目標也是有疑問的,因為這樣做既違背了其他國家的利益,也違背了在中國有強大市場的美國高科技企業的利益。在這樣的背景下,未來五年如果中國將其政策建立在美國政策會因自身矛盾而崩潰的假設之上,那將是一種天真、不切實際的戰略。因此,中國要向高收入經濟體邁進,就必須越來越多地依靠自己的技術。生產鏈的每一個環節都必須有可能在中國實現生產,最好的描述是“國內大循環”。我認為,這與1978年至2016年期間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進口技術的情況截然不同。當然,中國仍將繼續致力于全球化,這將是世界發展的最好路徑,并利用一切機會實現國際化。但在新形勢下,中國國內經濟將占據主導地位。
威廉·瓊斯:可以說,國際社會對中國“十四五”規劃的關注與眾不同。中國今年成為第一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有力且有效的國家。因此,在我看來,中國是第一個認真規劃2020年及未來幾年經濟復蘇之路的國家。全世界都在關注,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勢頭將決定世界經濟能否走出低迷。
實際上,中國有近14億人口,其中許多人仍處于中等收入水平以下,只要繼續努力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就有很大空間增加國內消費。正在進行中的扶貧攻堅戰就是為實現這個目的。然而,盡管國內消費仍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擴大開放”也使這種增長成為可能,并引起世界市場的極大興趣。前兩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參展情況表明,外國企業對中國市場非常感興趣。即使在這段災難性的新冠疫情時期和美國官員對投資者的負面壓力下,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也一直在增加,今年的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也即將舉行。這充分說明,中國高層提出的“雙循環”理念,即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一條正確的前進道路。
王文:和你們討論“十四五”規劃,我能感受到,中國的未來五年肯定將是又一個不容易的五年。但只要把握規律,保持定力,增強風險與機遇意識,發揚斗爭精神,善于在“危”中育新“機”,相信再過五年,中國又是一番全新的發展景象。(本文中文翻譯為楊清清、吳俁)